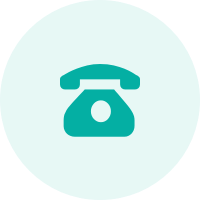预约国外,最快 1 个工作日回馈预约结果
2004年,我在大约两年内首次访问过的设施中访问了近100张床,并被一种不合理的感觉震惊。尽管我期望的是,几乎没有患者在两年前与我交谈。未出院。除了“死亡”之外,没有其他理由从该设施中消失...
2002年的Pavanapji。当时,这样的病人死了一天。 (我的照片,其他照片)
我是泰国中部洛布伯里郊区的帕瓦纳普-Ji寺(正式名称为“ wat phrabhatnamphu”。“ wat”表示这座寺庙。一些日本人很快将“ numpu -ji”称为“ numpu -ji”,但我们在这里首次访问” Pavanap -ji”)2002年,居民的第一年,暑假。当时,泰国没有抗HIV药物,艾滋病毒感染意味着“死亡”。该设施不是医院,而是寺庙。在泰国,有一个习惯赶往泰国的圣殿,而不得不等待死亡的患者变成了圣殿的僧侣,这变成了“艾滋病临终关怀”。
患者来到圣殿而不是医院,因为他们无需这样做就在医院付款。看来,没有抗HIV药物的医学专家可以做些事情,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时,泰国社会的“无知”疾病压倒了。实际上,我从Pavanapji的居民那里听到的故事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我无法冷静地写作。当我试图上公共汽车时,我被拖了下来。有人告诉他,当他在风中被扔掉时,他将被感染。他被赶出自助餐厅,扔了一道菜。我被家人抛弃,在街上徘徊...这样的故事没有时间。
我在居民第一年访问过的泰国的“决定生命的事件”
我想出了志愿服务的目的,以为居民的第一年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无事可做。但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两个“决定我生活的事件”。一个人是他遇到了比利时的GP博士,当时该设施活跃于该设施。 e博士的泰语不流利,但他仍然听症状和抱怨,并进行交流和治疗。许多患者患有疼痛,瘙痒,腹泻,呕吐和发烧。当然,您要寻找的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一种症状治疗。
Pavanapji寺的严重病房。其中约有30名严重患者。 (拍摄:2004年8月)
我很ham愧,我已经是一名医生,但是我不知道GP(全科医生)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决定从“ GP定义”中从博士那里学习。在欧洲,他并没有突然去一家大型医院的专家,像日本一样可以免费进入,而是一名GP和医生,并听到有关病人的任何抱怨。由于我还是一名学生,所以我想知道每次听到专家“不是我们的部门”时,我都想知道E.E博士的故事。这可能是我想要的。
我决定生活的另一件事是,我决定“彻底面对艾滋病毒疾病”。博士离开晚间设施后,我决定与患者交谈。但是,那时我根本无法说泰语。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一个在泰国工作的日本朋友作为口译员来。并非每个人都能听到这个故事,有些人已经患上了艾滋病毒脑病,有些人闭上了心,几乎不听。但是,总的来说,更多的人说:“我希望您听到这个故事。”我想介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患者。
这个女人的名字似乎已经20多岁了,是Meo(假名)。与艾滋病毒一起工作的丈夫已经去世并与一个生病的母亲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但是当地居民知道感染,当他的家人被歧视时。我离开了家。能够进入Pavanapji是一件好事,但是想到花费“暂停死亡”的生活只是渴望的。但是,在某一时刻,他将手放在一个难以行走的病人身上后发现了一种“生活的乐趣”。从那时起,它一直在擦拭其他患者并协助饭菜。在米饭补充时,我们采访了Meo。这项任务可用于打包全国各地捐赠的大米。毛说,自从他开始这项工作以来,他就逐渐获得了肌肉,并表现出右手的僵硬。
两年后,2004年。当时我在寻找微笑和微笑。当我在两年前回想起我的Pavanapji的店员时,我到了一个月才到达。他说,他一直在照顾其他患者,直到嘈杂。但是,幸存的母亲及其子女终于没有来到帕瓦纳普。
作者(中心)正在严重的病房中处理压力溃疡。中间女人是美国博士右边的女人是瑞典的照顾者。 (拍摄:2004年8月)
令人惊讶的是,博士走了。出于各种原因,他离开了帕瓦纳普-Ji庙,现在他正在泰国北部的艾滋病设施中志愿服务。相反,一位美国女医生J来了。她还说她也是GP。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学到了有关J.博士的基础知识。大约四个月,我在日本和泰国之间来回走动,但我积极向J和患者学习。大多数艾滋病指标可以在六个月内检查23种疾病,结核病和卡里尼肺炎(新的最霉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常见的疾病”。在日本,我们能够经历在日本很少报道的有价值的疾病,例如皮肤症状,cotocokas和penicillium。
与两年前相比,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免费提供抗HIV药物。即使这样,可以使用的药物类型也有限,即使由于副作用而无法使用,也没有其他选择。此外,并非所有人都得到了所有人,Pavanap的寺庙决定每月要服用哪个患者。我也参加了会议,但是我对没有知识或经验的我无话可说。在会议上,来自曼谷的艾滋病专家Wr.W博士熟悉当时在泰国使用的最新药物,但没有去找病人。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每天都在听患者的J博士并不比Wr.Wdr更好。但是我的榜样是J和Dr.E博士,这是离患者最接近的位置。
患者在温和的病房中。该中心是作者(照片:2004年8月)
返回日本后,我登上大阪市大阪大学通用学校。我决定正确学习初级保健。但是您可以在大学学习。除了大学外,我还决定在城市医院和从业人员学习。白天,他在大学医院,城市医院或诊所学习,并继续生活,主要是在晚上和周末,并继续在紧急门诊的日子里睡觉。但是,我每年三到四天休假三到四天,并参观了泰国的几个艾滋病设施。在日本,他很少检查艾滋病毒阳性患者,但艾滋病毒的疾病始终不在他的头上。
现在。在泰国,医疗专业人员歧视和偏见几乎消失了。很少有积极的人在工作中出来,但是在某些地区,甚至有些人关心整个社会的积极人。泰国的公众仍然存在歧视,但没有像2002年那样扔石头的方法,也无法在医疗机构面前付款。根据泰国医生的说法,几乎所有患者在第一次咨询中都要求艾滋病毒。
那在日本呢?艾滋病医疗医院的老师已提供最新的医疗服务。但是,艾滋病毒阳性人士不会立即去基地医院。您需要附近的家庭医生,但是有很多积极的人为他们找不到。您听说过多少次,当您告诉医疗机构您去过医院时,您说:“我不想让您来,因为您看不到它了。”
我真正想做的一件事是成为艾滋病毒阳性人群的家庭医生,这是在开放后立即意识到的。即使是现在,在几天里,艾滋病毒阳性的人没有咨询,有些人来自其他县,几个小时来转移火车来进行初级保健,例如感冒和腹部疼痛。我在家附近的一家基地医院进行定期咨询。没有理由有这种情况。不用说,您的家庭医生必须在您的家或工作场所附近。
日本医疗专业人员需要像泰国一样的泰国学徒改变。